《恒力报》微报纸二维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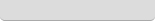
记忆中的炸藕饼
奶奶的炸藕饼,是带着声响的。那是一场热闹的、充满预示的交响——是老式铁锅铲在碗沿上“铛铛”的轻快磕碰,是筷子与陶盆壁“嗒嗒”的节奏摩擦。然后,“滋啦”一声,清亮决绝,是裹着淡金色面衣的藕饼滑入滚油时的欢呼。这声音,像一场盛宴的锣鼓,瞬间点燃满屋的期待。
奶奶用的是自家田里新掘的藕,她刨出的藕丝,绵长而任性,牵连着泥土最后的眷恋。她调的面糊,不过是面粉与水,但比例全在她那双布满纹路的手掌掂量之间。炸出的藕饼,外壳微咸焦香,内里藕片清甜脆嫩,再加上那似断非断的银丝,在唇齿间铺展开一片丰饶、立体的味觉旷野。
昨天,母亲在厨房里忙碌。她用的是不粘锅,手动打蛋器在不锈钢盆里旋转,发出均匀细密的“嗡嗡”声。藕饼下锅时,只有一声被油烟机吞掉大半的滋滋声,便再无波澜。我忽然明白,记忆里的“铛铛”与“滋啦”,是奶奶那个时代才有的,那是铁与陶、火与油最本真的碰撞,是不加修饰的生命力。
母亲的藕饼,用料更讲究,是超市里标着“九孔粉藕”的精品。面糊裹得匀净,炸得金黄一致。它很好吃,那层壳是整齐的酥,内里的藕是标准的糯,但没有狂野的丝,也没有意外的焦香。它像每个音符都精准的练习曲,却少了即兴的华彩乐章。
我嚼着母亲的藕饼,心里浮现出奶奶的样子。她总是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围裙,站在灶前,花白的头发被油烟气熏得微微颤动。她用那把笨重的铁锅铲,在油锅里灵巧地翻动,炸完一锅,她会夹起第一块,吹了又吹,递到眼巴巴守在一旁的我嘴边:“馋了吧,慢点,烫!”
奶奶的炸藕饼里,有柴火灶的旺火,有铁锅的镬气,有她一边忙活一边哼的不成调的小曲,更有她毫无保留的爱。所以我怀念的,又何止是一块藕饼?我怀念的,是那个在“铛铛”声里翘首以盼的、无忧无虑的自己;是那个厨房里氤氲的、带着油烟味的人间烟火;是那个总会为我吹凉第一口食物的、慈祥的身影。
奶奶走了,也带走了那个专属于她的吵闹而滚烫的世界。母亲做的炸藕饼,是一份充满爱意的延续,它抚慰我的胃,也清晰地丈量出,我与奶奶之间,那段再也无法跨越的时光深渊。那酥脆的余韵,终究在岁月里,散作唇齿间一缕悠长而怅惘的风。
文/郭栋琳(恒科新材料)(恒力集团版权所有,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)
奶奶用的是自家田里新掘的藕,她刨出的藕丝,绵长而任性,牵连着泥土最后的眷恋。她调的面糊,不过是面粉与水,但比例全在她那双布满纹路的手掌掂量之间。炸出的藕饼,外壳微咸焦香,内里藕片清甜脆嫩,再加上那似断非断的银丝,在唇齿间铺展开一片丰饶、立体的味觉旷野。
昨天,母亲在厨房里忙碌。她用的是不粘锅,手动打蛋器在不锈钢盆里旋转,发出均匀细密的“嗡嗡”声。藕饼下锅时,只有一声被油烟机吞掉大半的滋滋声,便再无波澜。我忽然明白,记忆里的“铛铛”与“滋啦”,是奶奶那个时代才有的,那是铁与陶、火与油最本真的碰撞,是不加修饰的生命力。
母亲的藕饼,用料更讲究,是超市里标着“九孔粉藕”的精品。面糊裹得匀净,炸得金黄一致。它很好吃,那层壳是整齐的酥,内里的藕是标准的糯,但没有狂野的丝,也没有意外的焦香。它像每个音符都精准的练习曲,却少了即兴的华彩乐章。
我嚼着母亲的藕饼,心里浮现出奶奶的样子。她总是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围裙,站在灶前,花白的头发被油烟气熏得微微颤动。她用那把笨重的铁锅铲,在油锅里灵巧地翻动,炸完一锅,她会夹起第一块,吹了又吹,递到眼巴巴守在一旁的我嘴边:“馋了吧,慢点,烫!”
奶奶的炸藕饼里,有柴火灶的旺火,有铁锅的镬气,有她一边忙活一边哼的不成调的小曲,更有她毫无保留的爱。所以我怀念的,又何止是一块藕饼?我怀念的,是那个在“铛铛”声里翘首以盼的、无忧无虑的自己;是那个厨房里氤氲的、带着油烟味的人间烟火;是那个总会为我吹凉第一口食物的、慈祥的身影。
奶奶走了,也带走了那个专属于她的吵闹而滚烫的世界。母亲做的炸藕饼,是一份充满爱意的延续,它抚慰我的胃,也清晰地丈量出,我与奶奶之间,那段再也无法跨越的时光深渊。那酥脆的余韵,终究在岁月里,散作唇齿间一缕悠长而怅惘的风。
文/郭栋琳(恒科新材料)(恒力集团版权所有,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)

 集团官网二维码
集团官网二维码 集团微信公众号
集团微信公众号